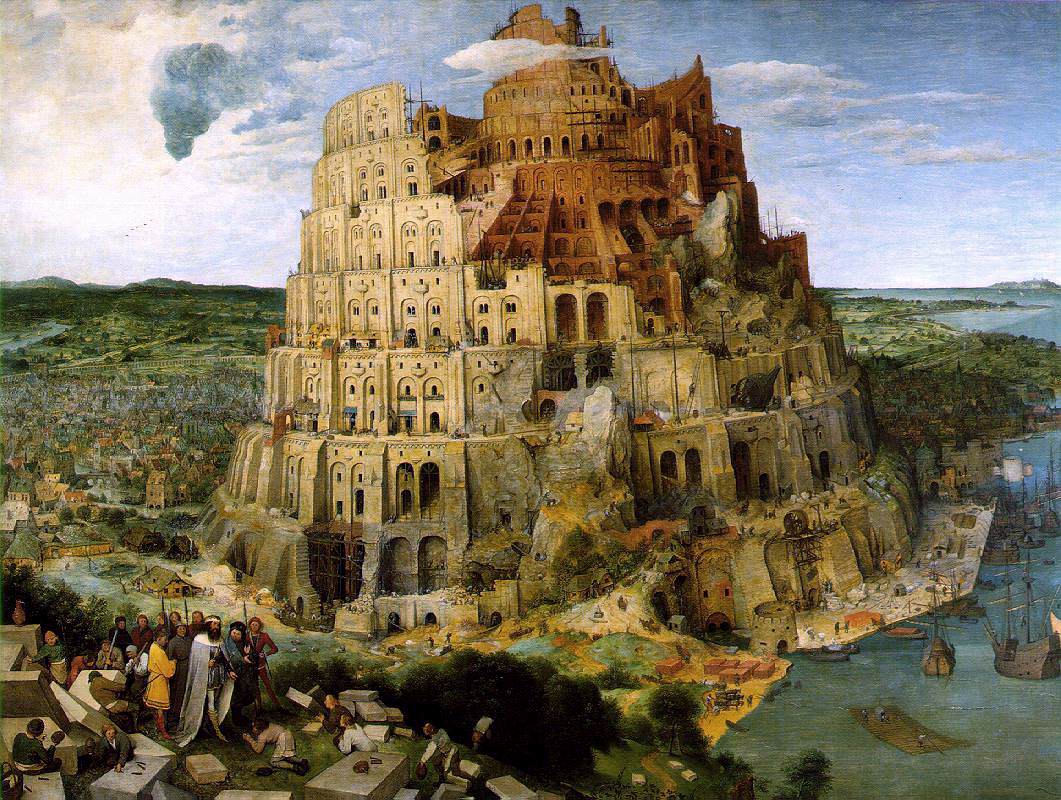|
| Meet the legend makers |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一
2011年12月23日 星期五
2011年12月20日 星期二
2011年12月5日 星期一
SLCD小傳
Spring-Loaded Camming Devices (SLCDs),在台灣大多數人用Wild Country的產品名:Friends來稱呼(大陸稱之為機械塞)。SLCD的發明在傳攀歷史上可說是劃時代的產物,它的發明讓傳攀活動更加便利、安全。但相較於傳統被動式的岩楔(nut/chock),SLCD在使用上仍有需多需加注意之處,尤其是其機械部分的保養跟使用,使用時若有疏忽則容易肇生事端。
以下文章譯自Climbing雜誌2011年2月號。
http://www.climbing.com/exclusive/features/10_things_you_didnt_know_about_camming_devices/
以下文章譯自Climbing雜誌2011年2月號。
(未經本人同意 ,請勿以任何形式張貼、轉載本文內容)
參考網址:http://www.climbing.com/exclusive/features/10_things_you_didnt_know_about_camming_devices/
2011年11月30日 星期三
半生
15歲甫接觸攀岩便技驚四座,現今邁入而立之年的Chris Sharma接受Climbing雜誌的專訪,回顧他的攀岩生涯並放眼展望未來,究竟Sharma還能帶給世人多少的驚嘆呢?
原文網址:http://www.climbing.com/exclusive/features/half_life/
(未經本人同意 ,請勿以任何形式張貼、轉載本文內容)
(未經本人同意 ,請勿以任何形式張貼、轉載本文內容)
Enzo的奇幻旅程
請回想,十五歲的你在做什麼?
十一歲的悟飯已經打敗塞魯,拯救了地球
十一歲的小傑走上萬里尋父的旅途(雖然跑去殺螞蟻)
十四歲的風見拿下閃電霹靂車冠軍
而來自法國的Enzo Oddo在十五歲那年完成攀岩生涯中第一條9a+路線
原文轉錄自Petzl官網
2011年10月25日 星期二
2011年9月29日 星期四
2011年8月29日 星期一
2011年8月2日 星期二
2011年7月27日 星期三
2011年5月29日 星期日
2011年5月24日 星期二
綠堤之外
跟大家分享一點心情。
也許有人還記得Gisel,前陣子偶爾會在岩場出現的墨西哥女孩。
練過啦啦隊的她,柔軟度非常好,雖然力量不強,但爬幾次之後已經可以top rope上岩場的頂端。每次看到她都笑容滿面,我懷疑她根本就是人造人,身體裝有反應爐才能如此充滿活力。
攀岩在政大已經退流行了,可這個中文夾雜特殊腔調的外國人卻是很喜歡到岩場,儘管有時整下午爬不到兩趟。這一個月來我很少跟她見面,但她幾乎每週都固定會寄信問我要不要去蘭州街,她想去動動筋骨,雖然她也只能爬白色路線,但看得出她真的很喜歡這項運動。
今天早上我例行性的寄信問星期三晚上要不要去動一下,儘管我覺得這星期大概又是碰不到面。結果她剛剛回信跟我說,她打工時出了狀況,手被切番茄
的機器捲到,差點保不住手指,目前應該是被醫生縫回去在家養傷。
沒問是哪隻手受傷,切到幾根手指。
我覺得我真是白痴,在這節骨眼居然還問她要不要去攀岩。
我記憶力很差,印象中這學期除了猴子、阿衝這兩個老班底以外,就只有Gisel老是問我什麼時候要爬岩,她想一起去爬。而現在孤單的岩牆似乎又要少一個朋友。
我沒那勇氣問她什麼時候會康復,到時再回來一起爬岩。
但我會把繩子架好等她。
這是個很沒來由的心情。只是希望在校的各位下次摸到這塊牆,也許可以想起一些不一樣的小故事。
也許有人還記得Gisel,前陣子偶爾會在岩場出現的墨西哥女孩。
練過啦啦隊的她,柔軟度非常好,雖然力量不強,但爬幾次之後已經可以top rope上岩場的頂端。每次看到她都笑容滿面,我懷疑她根本就是人造人,身體裝有反應爐才能如此充滿活力。
攀岩在政大已經退流行了,可這個中文夾雜特殊腔調的外國人卻是很喜歡到岩場,儘管有時整下午爬不到兩趟。這一個月來我很少跟她見面,但她幾乎每週都固定會寄信問我要不要去蘭州街,她想去動動筋骨,雖然她也只能爬白色路線,但看得出她真的很喜歡這項運動。
今天早上我例行性的寄信問星期三晚上要不要去動一下,儘管我覺得這星期大概又是碰不到面。結果她剛剛回信跟我說,她打工時出了狀況,手被切番茄
的機器捲到,差點保不住手指,目前應該是被醫生縫回去在家養傷。
沒問是哪隻手受傷,切到幾根手指。
我覺得我真是白痴,在這節骨眼居然還問她要不要去攀岩。
我記憶力很差,印象中這學期除了猴子、阿衝這兩個老班底以外,就只有Gisel老是問我什麼時候要爬岩,她想一起去爬。而現在孤單的岩牆似乎又要少一個朋友。
我沒那勇氣問她什麼時候會康復,到時再回來一起爬岩。
但我會把繩子架好等她。
這是個很沒來由的心情。只是希望在校的各位下次摸到這塊牆,也許可以想起一些不一樣的小故事。
2011年4月28日 星期四
2011四川駱駝峰移地訓練誌 (後記)
4/7 Day7: C1-->布羅德峰
「有一種人,他會選擇走一條不是預期中的路,甚至走到了路的盡頭,明明已經沒有路可以走了,他卻還可以走道路的盡頭之後,這種人叫做『探險者』。一個人要走到路的盡頭可能需要許多的堅持與耐心。但是,一位探險者要走出盡頭之外,則需要絕對的勇氣,以及,對於生命不同想像的渴望,因為他想要看見盡頭之後的風景,而且,他不認為盡頭就是盡頭。」
《勇氣,在山盡頭》
2011年4月16日 星期六
2011年4月15日 星期五
2011四川駱駝峰移地訓練誌 (V)
2011四川駱駝峰移地訓練誌 (IV)
2011年4月14日 星期四
2011四川駱駝峰移地訓練誌 (III)
2011年4月11日 星期一
2011四川駱駝峰移地訓練誌 (II)
2011年4月10日 星期日
2011四川駱駝峰移地訓練誌 (I)
4/1 Day1: 台北-->成都 (宿交通飯店)
前晚因為裝備始終點不齊,深怕少支螺旋冰錐、缺根岩釘,到時會影響到團隊攻頂的進度;二方面總是擔心自己禦寒衣物、手套、糧食有缺漏;三方面是太久沒出國,這次要隨歐都納八千米團隊移地至中國四川的四姑娘山區訓練,心裡總是覺得忐忑不安。在沒睡幾小時的情況下,起了個大早就拖著沉甸甸的行李袋到宿舍外等計程車前來接送。
跟元植、冠洲大哥到機場後,其他隊員也陸陸續續抵達,看到眾人直接在機場清點裝備,有種軍容浩蕩之感。秀真姊為移訓特地準備硬底鞋、小小黑也借來各色冰雪攀器材,而啟宏更是帶著專業的相機,準備為這次訓練做最詳盡的紀錄。
 |
拍過團體照後搭機正式出發,大家在機上也不忘展現活力。 |
2011年3月24日 星期四
關於冒險
「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這讓我想到我每次總是跟爸媽說要去爬山但他們很少知道到底我身在台灣哪個角落。為什麼在科技昌明的時代,還有人要放下GPS,遠離道路跟大眾運輸系統,冒著生命危險走進窮山惡水?沒有人想拿命當賭注,我也相信沒有人意圖讓家人悲傷。那究竟是為了什麼原因要去登山呢?難道只因為「山在那裡」,人們就要去冒險嗎?對山野環境的未知、陌生感導致人們在城市/曠野這樣的空間中化出了無法跨越的空白與鴻溝。一月底第一堂課,黃老師就要我們思考死亡議題。登山的確是有其風險,且成敗常以生死定論。「喜瑪拉雅的愛與死」裡面,倖存的張銘隆回到基地營後精疲力盡,只得聽到隊友在兩天近乎空白的時間,不斷在山裡未知的角落發出呼救。這種無能為力的恐懼,有可能是每位登山者都會遇到的課題。往聖母峰頂的路上,有位登山者腦水腫發作,但來來往往的攻頂者、雪巴無人伸出援手,只得讓他活活在原地凍死。難道八千米以上的絕境真沒有倫理嗎?無論是迷途、遭遇雪崩、墜落,我都想知道那些在也無法與家人見面的罹難者在最後一刻腦中想著什麼。他們後悔踏上這條不歸路嗎?心痛嗎?是否心生怯懦呢?是否眷戀心愛之人的甜美笑容?
實在不喜歡「冒險」一詞,因為很容易被解讀為「找死」,對那些生命安逸或不曾思考如何突破侷限的人而言,走出自我構築的世界是相當艱難的一步。當年哥倫布船隊上所載糧食財寶、輜重器具,不用遇到海怪或盜賊,只要一晚的暴風雨就可能悉數烏有。如果葡萄牙王室怕浪費公帑,如果哥倫布只想念個大學文憑畢業然後考個高考窩在某個政府機構角落過一生,到現在這世界可能還是平的,而海洋兩端盡頭各有巨獸盤據、張開血盆大口準備吞試過路商旅。
「冒險」意涵著探索。英語adventure與expedition兩詞皆意涵著向前方行走、向未知走去、向幽冥渺渺走去。由此看來,玄奘西行是冒險、達加傌環球而行是冒險、亞歷山大東征也是冒險。除了顯著的事蹟以外,這些冒險家都代表著開創特定時代的精神。也許玄奘取經的工作可以交由他人完成,因為記錄、目標只會不斷被刷新,但難道我們會因為高爆性炸藥的推陳出新,而否定諾貝爾發明的硝化甘油炸藥?不會的,因為唯有站在巨人的肩上,才能看的更遠。
友人們以為我參加八千米計畫是想創記錄,想成為第一人,想當台灣之光。其實我的動機很單純,我只想上去看看巴托羅冰河緩緩移動,看看兩倍玉山的高度是怎樣的視野。這動機單純,但要完成這目標所牽涉到的知識、技巧卻是複雜無比。我必須進重訓室練股四頭肌跟手臂肌肉,開始學練跑馬拉松好讓心肺力足以負荷低壓以及空氣中稀薄的氧氣。我必須學著看雲圖、氣壓圖、風向圖,有的沒的圖,只為了抓住三、四小時的晴天空窗,或試著避開風暴。我必須翻開厚重的登山史,念那些敖牙的日、韓、英文人名跟事蹟。
我一直告訴自己,過程才是重點,即使結果失敗,我都會覺得我成功了,因為我沒有放棄,而且我學到很多先前忽略的東西。
這就是我的冒險。
實在不喜歡「冒險」一詞,因為很容易被解讀為「找死」,對那些生命安逸或不曾思考如何突破侷限的人而言,走出自我構築的世界是相當艱難的一步。當年哥倫布船隊上所載糧食財寶、輜重器具,不用遇到海怪或盜賊,只要一晚的暴風雨就可能悉數烏有。如果葡萄牙王室怕浪費公帑,如果哥倫布只想念個大學文憑畢業然後考個高考窩在某個政府機構角落過一生,到現在這世界可能還是平的,而海洋兩端盡頭各有巨獸盤據、張開血盆大口準備吞試過路商旅。
「冒險」意涵著探索。英語adventure與expedition兩詞皆意涵著向前方行走、向未知走去、向幽冥渺渺走去。由此看來,玄奘西行是冒險、達加傌環球而行是冒險、亞歷山大東征也是冒險。除了顯著的事蹟以外,這些冒險家都代表著開創特定時代的精神。也許玄奘取經的工作可以交由他人完成,因為記錄、目標只會不斷被刷新,但難道我們會因為高爆性炸藥的推陳出新,而否定諾貝爾發明的硝化甘油炸藥?不會的,因為唯有站在巨人的肩上,才能看的更遠。
友人們以為我參加八千米計畫是想創記錄,想成為第一人,想當台灣之光。其實我的動機很單純,我只想上去看看巴托羅冰河緩緩移動,看看兩倍玉山的高度是怎樣的視野。這動機單純,但要完成這目標所牽涉到的知識、技巧卻是複雜無比。我必須進重訓室練股四頭肌跟手臂肌肉,開始學練跑馬拉松好讓心肺力足以負荷低壓以及空氣中稀薄的氧氣。我必須學著看雲圖、氣壓圖、風向圖,有的沒的圖,只為了抓住三、四小時的晴天空窗,或試著避開風暴。我必須翻開厚重的登山史,念那些敖牙的日、韓、英文人名跟事蹟。
我一直告訴自己,過程才是重點,即使結果失敗,我都會覺得我成功了,因為我沒有放棄,而且我學到很多先前忽略的東西。
這就是我的冒險。
2011年3月23日 星期三
下個十年
當天晚了一點到,實在不好意思
看到教室角落有幾個生面孔,不知是不是還未上板自介的新隊員?
當天學長提到他1992年入政大時就加入山隊 (那時我8歲)
對於山隊年表可能現在在校生不熟,我就我所知大略複習一下:
1972年(民國61年)政大登山隊成立。那是個還流行大粗框眼鏡的年代。
聽老烏鴉說,以前開領隊會議都要找地方窩起來開會,
因為那時禁止秘密結社。迄今仍是台灣大專院校唯一登
山校隊。
1992年(民國81年)志展學長進入山隊,約莫是山隊二十週年隊慶。現在慕
峰辦公室還掛著張當年民生報的剪報。而民生報幾年前
已經倒了。
2002年(民國91年)算一算是學長爬山十年,是年舉行中央山脈大縱走後於
南湖圈谷與真秀學姊結婚。
2011年(民國100年)學長回母校與山隊學弟妹分享經驗。籌劃的14座八千米
巨峰探險計畫正式啟動,將以十年以上時間探索喜瑪拉雅
、喀喇崑崙山區的山峰。今年也恰好是山隊四十週年隊慶。
這中間有許多的巧合,十年一期的發生一些事情,不但是學長個人登山生涯的
一些轉捩點,也甚至是山隊為人津津樂道的隊史。
其實我是當晚才知道學長改分享題目,不過後來想說可能是學長前陣子一直聽我
抱怨現在山隊人很少,所以學長想用他的親身經歷激勵一下大家。
當天學長提了些人名,可能大家聽過去沒印象或沒感覺,讓我補完一下:
溯馬太鞍溪時,學長提到有個王伯宇學長掉進深潭。當時氣氛輕鬆所以大家笑笑帶
過,但這位學長其實是山隊攀岩風氣全盛時期的人物之一,也曾獲選攀岩國手。
同隊的還有清鋐跟阿爹。清鋐去年才到南美洲騎單車遊歷了半年;而阿爹是老歸
老,但沒事就會拿連下12天雨的馬太鞍溪行出來講,可見該隊精采之程度,足以
讓人回味(嘴砲?)近十年不衰。
後來的中央山脈大縱走,除了新人以外,陪走的名單裡也有清鋐,所以各位就知道
登山隊在校生中央山脈大縱走這記錄已經寫上別人名字了,以後要想留名要玩更大
的才行。在校生登頂高度記錄是1996年慕士塔格峰的7,546公尺,由當時在校的
宋一炘、林宏明創下,所以下個想創記錄的快去找志展學長報名。
志展學長說他進山隊時洽逢青黃不接時期,但他畢業(後),山隊其實又有一波
生命力蓬勃的新秀崛起。這次回校分享,不為了炫耀豐功偉業,只想跟學弟妹分
享一種「登山的精神」。這聽起來非常抽象,但根據學長的描述,那就是一種走
在邊緣的壓力感,心靈感到負荷但是精神卻無比自由。「有願就有力」,這是學
長近二十年的登山心得。
(後記)
前陣子因為參加活動,也算是因緣際會的跟志展學長比較有接觸,同時也接觸到
現在在中央財金系任教的中達學長(誰說爬山書就讀不好?)。其實先前也曾見過
學長幾次,但了解不多。後來才知道中達學長是1982年首攀玉山北壁岩溝的隊員之一
,往後三十年間,學長與台灣的攀岩、遠征活動幾乎孟不離焦。除了身為龍洞天然
岩場的開發者之一以外,1996年523登山會的慕士塔格峰遠征隊擔任隊長,10年後的
七頂峰、八千米計畫擔任顧問。從中達學長到志展學長身上,我的確看到了不同世
代在當下的交疊。不同的世代具有共同的精神:開創!向未知走去、往極限挑戰,
是在這些登山活動隱含的唯一目標。
註:
1.本文內容主要根據上課記憶寫出,如果疏漏、謬誤,請不吝指正。
2.有關攀岩史的部份主要參考「台灣攀岩運動發展之研究1945~2006」(李潛龍 2008)http://ppt.cc/LV;W 。很驚訝發現,政大附設幼稚園是全台灣最早有室內攀岩場的幼稚園,我猜想這跟山隊的影響也許有關(政大岩場後建於1997年)。
此文撰於第十三屆政大盃攀岩賽以及政大山隊四十週年隊慶前夕。
看到教室角落有幾個生面孔,不知是不是還未上板自介的新隊員?
當天學長提到他1992年入政大時就加入山隊 (那時我8歲)
對於山隊年表可能現在在校生不熟,我就我所知大略複習一下:
1972年(民國61年)政大登山隊成立。那是個還流行大粗框眼鏡的年代。
聽老烏鴉說,以前開領隊會議都要找地方窩起來開會,
因為那時禁止秘密結社。迄今仍是台灣大專院校唯一登
山校隊。
1992年(民國81年)志展學長進入山隊,約莫是山隊二十週年隊慶。現在慕
峰辦公室還掛著張當年民生報的剪報。而民生報幾年前
已經倒了。
2002年(民國91年)算一算是學長爬山十年,是年舉行中央山脈大縱走後於
南湖圈谷與真秀學姊結婚。
2011年(民國100年)學長回母校與山隊學弟妹分享經驗。籌劃的14座八千米
巨峰探險計畫正式啟動,將以十年以上時間探索喜瑪拉雅
、喀喇崑崙山區的山峰。今年也恰好是山隊四十週年隊慶。
這中間有許多的巧合,十年一期的發生一些事情,不但是學長個人登山生涯的
一些轉捩點,也甚至是山隊為人津津樂道的隊史。
其實我是當晚才知道學長改分享題目,不過後來想說可能是學長前陣子一直聽我
抱怨現在山隊人很少,所以學長想用他的親身經歷激勵一下大家。
當天學長提了些人名,可能大家聽過去沒印象或沒感覺,讓我補完一下:
溯馬太鞍溪時,學長提到有個王伯宇學長掉進深潭。當時氣氛輕鬆所以大家笑笑帶
過,但這位學長其實是山隊攀岩風氣全盛時期的人物之一,也曾獲選攀岩國手。
同隊的還有清鋐跟阿爹。清鋐去年才到南美洲騎單車遊歷了半年;而阿爹是老歸
老,但沒事就會拿連下12天雨的馬太鞍溪行出來講,可見該隊精采之程度,足以
讓人回味(嘴砲?)近十年不衰。
後來的中央山脈大縱走,除了新人以外,陪走的名單裡也有清鋐,所以各位就知道
登山隊在校生中央山脈大縱走這記錄已經寫上別人名字了,以後要想留名要玩更大
的才行。在校生登頂高度記錄是1996年慕士塔格峰的7,546公尺,由當時在校的
宋一炘、林宏明創下,所以下個想創記錄的快去找志展學長報名。
志展學長說他進山隊時洽逢青黃不接時期,但他畢業(後),山隊其實又有一波
生命力蓬勃的新秀崛起。這次回校分享,不為了炫耀豐功偉業,只想跟學弟妹分
享一種「登山的精神」。這聽起來非常抽象,但根據學長的描述,那就是一種走
在邊緣的壓力感,心靈感到負荷但是精神卻無比自由。「有願就有力」,這是學
長近二十年的登山心得。
(後記)
前陣子因為參加活動,也算是因緣際會的跟志展學長比較有接觸,同時也接觸到
現在在中央財金系任教的中達學長(誰說爬山書就讀不好?)。其實先前也曾見過
學長幾次,但了解不多。後來才知道中達學長是1982年首攀玉山北壁岩溝的隊員之一
,往後三十年間,學長與台灣的攀岩、遠征活動幾乎孟不離焦。除了身為龍洞天然
岩場的開發者之一以外,1996年523登山會的慕士塔格峰遠征隊擔任隊長,10年後的
七頂峰、八千米計畫擔任顧問。從中達學長到志展學長身上,我的確看到了不同世
代在當下的交疊。不同的世代具有共同的精神:開創!向未知走去、往極限挑戰,
是在這些登山活動隱含的唯一目標。
註:
1.本文內容主要根據上課記憶寫出,如果疏漏、謬誤,請不吝指正。
2.有關攀岩史的部份主要參考「台灣攀岩運動發展之研究1945~2006」(李潛龍 2008)http://ppt.cc/LV;W 。很驚訝發現,政大附設幼稚園是全台灣最早有室內攀岩場的幼稚園,我猜想這跟山隊的影響也許有關(政大岩場後建於1997年)。
此文撰於第十三屆政大盃攀岩賽以及政大山隊四十週年隊慶前夕。
給學長
學長:
其實我沒見過你,你應該也還沒聽過我的名字就先走一步。
山隊從游泳池搬到司令台樓上也超過五年,而你也大約是那個時間點離開我們。
記得搬山房時,在成堆的資料中我有瞥見過岩場的設計圖,要說岩場每一根螺絲是你跟其他學長姊的心血結晶也不為過。岩場建成十五年,而這週末就要辦第十三屆政大盃。如果說岩場也是你的子女,那今年差不多要升高中了。在這樣的時刻,你卻不能夠在我們身邊,實在遺憾。
記得看到岩場藍圖那年,我根本連岩塊都沒摸過。攀岩對當時的我來是遙不可及的運動:孤單又步步驚險。曾幾何時我也從只能摸兩、三顆岩點,到現在至少還可以爬爬簡單路線,雖然不像學長在岩壁上那樣自在、從容,但勉強還能活動活動筋骨,順便向新加入的學弟妹臭屁一下,博取激賞的眼光。
現在的學弟妹都很喜歡爬山,不過他們太專心了,都沒人願意分心來攀攀岩。岩場前幾天剛讓拔山的師父換新支架,看來又可以再撐十五年。今天去拔山跟聰哥拿切割器,拔山也變很多,空間比以前大多了。雖然不像老猴可以跟你買件Gore-Tex外套後每次出隊都跟我們炫耀,不過以後有機會也可以學學怎麼釘鋼架、怎樣裁木板、鑽螺孔。等我們把山房拿回來,我就要在裡面重蓋個抱石場,以後讓學弟妹每學期都辦山房盃抱石賽。
今天稍微看了一下當年慕峰遠征的裝備,冰爪都還很新呢,爪尖似乎還沾著初融的雪水。今年就先讓我帶它們去駱駝峰解解渴吧,等年底,年底523跟山隊又要動起來了,年底就可以再相聚。
岩場頂燈壞了有一陣子,打去營繕組報修,不知怎地從人身安全又提到你的名字。也許是有人覺得惋惜吧?你最愛的攀岩帶走了你,但我相信他不知道,其實你一直都在。
每一個椰影搖曳的夏日、每一個明月高掛的夜晚,你都還在這裡守候,不曾離開。
其實我沒見過你,你應該也還沒聽過我的名字就先走一步。
山隊從游泳池搬到司令台樓上也超過五年,而你也大約是那個時間點離開我們。
記得搬山房時,在成堆的資料中我有瞥見過岩場的設計圖,要說岩場每一根螺絲是你跟其他學長姊的心血結晶也不為過。岩場建成十五年,而這週末就要辦第十三屆政大盃。如果說岩場也是你的子女,那今年差不多要升高中了。在這樣的時刻,你卻不能夠在我們身邊,實在遺憾。
記得看到岩場藍圖那年,我根本連岩塊都沒摸過。攀岩對當時的我來是遙不可及的運動:孤單又步步驚險。曾幾何時我也從只能摸兩、三顆岩點,到現在至少還可以爬爬簡單路線,雖然不像學長在岩壁上那樣自在、從容,但勉強還能活動活動筋骨,順便向新加入的學弟妹臭屁一下,博取激賞的眼光。
現在的學弟妹都很喜歡爬山,不過他們太專心了,都沒人願意分心來攀攀岩。岩場前幾天剛讓拔山的師父換新支架,看來又可以再撐十五年。今天去拔山跟聰哥拿切割器,拔山也變很多,空間比以前大多了。雖然不像老猴可以跟你買件Gore-Tex外套後每次出隊都跟我們炫耀,不過以後有機會也可以學學怎麼釘鋼架、怎樣裁木板、鑽螺孔。等我們把山房拿回來,我就要在裡面重蓋個抱石場,以後讓學弟妹每學期都辦山房盃抱石賽。
今天稍微看了一下當年慕峰遠征的裝備,冰爪都還很新呢,爪尖似乎還沾著初融的雪水。今年就先讓我帶它們去駱駝峰解解渴吧,等年底,年底523跟山隊又要動起來了,年底就可以再相聚。
岩場頂燈壞了有一陣子,打去營繕組報修,不知怎地從人身安全又提到你的名字。也許是有人覺得惋惜吧?你最愛的攀岩帶走了你,但我相信他不知道,其實你一直都在。
每一個椰影搖曳的夏日、每一個明月高掛的夜晚,你都還在這裡守候,不曾離開。
2011年3月22日 星期二
山的意志
今天稍晚到523,剛出電梯就聞到空氣中那股濃濃高粱味,加上迴盪在樓梯間內的笑鬧聲,想必學長們又喝開了。進去才發現,滿座學長姊比我預期的數量還多一點。中達、阿展學長都到了,剛進門就被奕炘學長拉到旁邊去,要我試穿他的雙重靴。
只見學長拿出一個鞋箱,上面印著Millet。「這...不會吧?」我心裡是無限的詫異,我本來以為學長用的是慕峰遠征時代的靴子,但看這紙箱還十分新穎,連邊角都沒有折凹。只見學長打開鞋盒後緩緩撥開兩層薄紙,傳說中的Everest GTX就躺在裡面。那瞬間我心裡實在是無比的驚訝。一方面因為我完全沒意料有機會借到著麼高檔的裝備,二來是學長居然大方的要借我這雙鞋。其實當下我是被嚇傻的,因為這真的太突然了,只見學長督促著我快點試穿,我倒是有點楞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可惜的是,這雙鞋稍小了些,穿太緊到了高海拔血液循環一差,四肢很容易凍傷,只能用羨慕眼光將鞋子還回。
在惋惜之餘,安兄拿起了另一袋雙重靴,是他去慕峰時穿的(十五年!!!),除了小部分裂開以外,靴身狀況看起來還是不差。學長很豪氣的說要送給我(儘管是陳年老靴,新品重買也要兩萬左右),看來這次四川移地訓練我有鞋子可以替換使用了。
離開學校前,荏元塞給我一包他親調的生脈散 ,說是可以增強心脈、幫助適應高海拔氣壓。本來說好要均分藥材費用,不過學長看我已經為了四川旅費焦頭爛額,就乾脆整罐送我當贊助移地訓練,讓我有點不好意思。
晚上聊到山隊四十週年的遠征計畫,談了些西藏、尼泊爾的山峰,但一直沒有個定案。這時賴桑已經有些微醺,直喊著要去爬山。後來講到當年慕峰,賴桑似乎因為體力支持不住所以放棄攻頂,我想他心裡多少帶有遺憾。後來四川、希夏邦馬、阿馬達布朗...每個山名都被提過一輪,只看學長的眼睛瞪的老大,兩眼炯炯有神,想必是心裡沉歇十五年的熱情又被攪動。
約莫十二點離開時,安兄又跑回機車上拿了副Windstopper的手套給我,是慕峰遠征的裝備。本來想用我的Snow Travel跟學長換,好歹騎車有個擋風手套,學長卻說他家裡還有一副。我當下相信了,但直到現在才想到,誰沒事會買兩副Windstopper手套?況且,從古亭騎回民生社區還是有段距離,而被冷氣團籠罩的台北正下著陰濕小雨。
這晚我獲得很多的祝福與力量,希望未來能夠將這些鼓勵、感動,化為我前行的動力。
感謝有你們。
與你們同在,與山同在。
只見學長拿出一個鞋箱,上面印著Millet。「這...不會吧?」我心裡是無限的詫異,我本來以為學長用的是慕峰遠征時代的靴子,但看這紙箱還十分新穎,連邊角都沒有折凹。只見學長打開鞋盒後緩緩撥開兩層薄紙,傳說中的Everest GTX就躺在裡面。那瞬間我心裡實在是無比的驚訝。一方面因為我完全沒意料有機會借到著麼高檔的裝備,二來是學長居然大方的要借我這雙鞋。其實當下我是被嚇傻的,因為這真的太突然了,只見學長督促著我快點試穿,我倒是有點楞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可惜的是,這雙鞋稍小了些,穿太緊到了高海拔血液循環一差,四肢很容易凍傷,只能用羨慕眼光將鞋子還回。
在惋惜之餘,安兄拿起了另一袋雙重靴,是他去慕峰時穿的(十五年!!!),除了小部分裂開以外,靴身狀況看起來還是不差。學長很豪氣的說要送給我(儘管是陳年老靴,新品重買也要兩萬左右),看來這次四川移地訓練我有鞋子可以替換使用了。
離開學校前,荏元塞給我一包他親調的生脈散 ,說是可以增強心脈、幫助適應高海拔氣壓。本來說好要均分藥材費用,不過學長看我已經為了四川旅費焦頭爛額,就乾脆整罐送我當贊助移地訓練,讓我有點不好意思。
晚上聊到山隊四十週年的遠征計畫,談了些西藏、尼泊爾的山峰,但一直沒有個定案。這時賴桑已經有些微醺,直喊著要去爬山。後來講到當年慕峰,賴桑似乎因為體力支持不住所以放棄攻頂,我想他心裡多少帶有遺憾。後來四川、希夏邦馬、阿馬達布朗...每個山名都被提過一輪,只看學長的眼睛瞪的老大,兩眼炯炯有神,想必是心裡沉歇十五年的熱情又被攪動。
約莫十二點離開時,安兄又跑回機車上拿了副Windstopper的手套給我,是慕峰遠征的裝備。本來想用我的Snow Travel跟學長換,好歹騎車有個擋風手套,學長卻說他家裡還有一副。我當下相信了,但直到現在才想到,誰沒事會買兩副Windstopper手套?況且,從古亭騎回民生社區還是有段距離,而被冷氣團籠罩的台北正下著陰濕小雨。
這晚我獲得很多的祝福與力量,希望未來能夠將這些鼓勵、感動,化為我前行的動力。
感謝有你們。
與你們同在,與山同在。
2011年3月21日 星期一
8848.28的高度
珠穆朗瑪峰,又稱聖母峰。高8848公尺,為世界第一高峰。
昨晚到福和國中聽七頂峰探險隊隊員伍玉龍、同行拍攝紀錄片的柯導,以及兩位在前些時段完成中央山脈大縱走的年輕人分享登山經驗。雖然在場與會人員出乎我意料的多,但大多還是叔姪輩的登山愛好者。
伍大哥主要是針對歐都那贊助的七頂峰探險行程作介紹,七頂峰分別是:
亞洲:珠穆朗瑪峰 8848公尺
歐洲:厄爾布魯士峰:海拔5642公尺
非洲:吉力馬札羅山:海拔5895公尺
北美洲:麥肯尼峰:海拔6194公尺
南美洲:阿空加瓜山:海拔6962公尺
大洋洲:卡茲登茲峰:海拔4884公尺
南極洲:文森山峰:海拔4892公尺
伍大哥主要是針對歐都那贊助的七頂峰探險行程作介紹,七頂峰分別是:
亞洲:珠穆朗瑪峰 8848公尺
歐洲:厄爾布魯士峰:海拔5642公尺
非洲:吉力馬札羅山:海拔5895公尺
北美洲:麥肯尼峰:海拔6194公尺
南美洲:阿空加瓜山:海拔6962公尺
大洋洲:卡茲登茲峰:海拔4884公尺
南極洲:文森山峰:海拔4892公尺
能夠攀爬其中一座,是所有登山者的夢想;而得允踏上這七座高峰的峰頂,更是極少數人能得到的殊榮。對不諳登山活動的人而言,攀登七頂峰也許只是一次成功的企業宣傳,但對喜歡、愛好、熱衷登山的登山者來說,七頂峰的意義非凡,並不僅是成功攀登七座高峰而已。
其實分享時沒想太多,到現在腦中才有一些想法跟問題想要請教遠征七頂峰的隊員:登上聖母峰時你的第一個想法是甚麼?完攀七頂峰後,你覺得是甚麼原因促使你堅持下去?你覺得你的人生或是想法有何改變?
依照普通的登山模式,在攻頂(百岳)後除了歡呼以外,第一件事是拿出隊旗(如果有)拍照,接著是拿些點心小乾糧吃,想爽爽過的會拿出爐頭煮水泡茶。但我想知道,如果我今天背著氧氣瓶跟負荷重裝的背包,歷經千辛萬苦後終於登頂,登頂後我要做甚麼?在空氣稀薄、雲影飄渺的頂點,氣溫始終低於零下三十度的地方,我還能思考嗎?
其實分享時沒想太多,到現在腦中才有一些想法跟問題想要請教遠征七頂峰的隊員:登上聖母峰時你的第一個想法是甚麼?完攀七頂峰後,你覺得是甚麼原因促使你堅持下去?你覺得你的人生或是想法有何改變?
依照普通的登山模式,在攻頂(百岳)後除了歡呼以外,第一件事是拿出隊旗(如果有)拍照,接著是拿些點心小乾糧吃,想爽爽過的會拿出爐頭煮水泡茶。但我想知道,如果我今天背著氧氣瓶跟負荷重裝的背包,歷經千辛萬苦後終於登頂,登頂後我要做甚麼?在空氣稀薄、雲影飄渺的頂點,氣溫始終低於零下三十度的地方,我還能思考嗎?